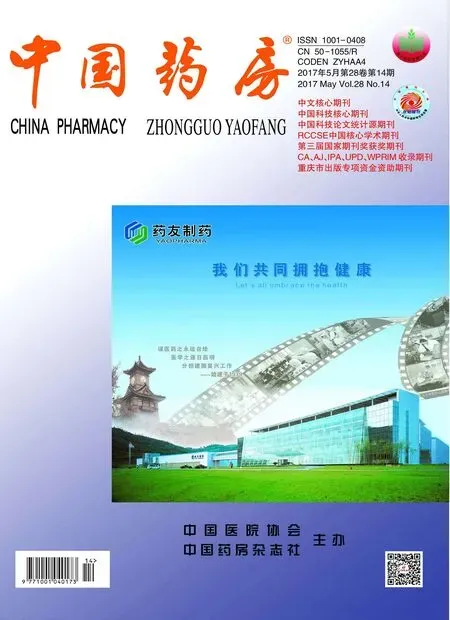中國藥房
精準(zhǔn)醫(yī)療
藥物經(jīng)濟(jì)學(xué)
用藥分析與評(píng)價(jià)
臨床藥學(xué)與研究
不良反應(yīng)與監(jiān)測
藥物與臨床
- 腎福康膠囊治療腎功能不全的臨床研究Δ
- 丹參酮聯(lián)合角膜緣干細(xì)胞移植術(shù)治療翼狀胬肉的臨床觀察Δ
- 鴉膽子油聯(lián)合吉西他濱和順鉑治療晚期非小細(xì)胞肺癌的臨床觀察Δ
- 不同劑量瑞舒伐他汀治療急性腦梗死的臨床觀察Δ
- 氯雷他定口服聯(lián)合生理性海水鼻腔沖洗治療間歇性變應(yīng)性鼻炎的臨床研究
- 獨(dú)活寄生湯聯(lián)合硫酸氨基葡萄糖治療膝骨性關(guān)節(jié)炎的臨床觀察
- 利拉魯肽聯(lián)合胰島素和格列吡嗪治療亞甲減合并2型糖尿病老年患者的臨床研究
- 復(fù)方鱉甲軟肝片聯(lián)合恩替卡韋片對(duì)慢性乙型肝炎瘀血阻絡(luò)證型患者肝功能及膽紅素的影響
- 非洛地平緩釋片(Ⅱ)治療老年原發(fā)性高血壓的臨床觀察
- 醋酸戈舍瑞林緩釋植入劑治療術(shù)后復(fù)發(fā)卵巢內(nèi)膜囊腫的臨床觀察
- 兩種糖皮質(zhì)激素給藥方案治療老年AECOPD患者的臨床觀察
- 膿毒血癥患者應(yīng)用丙氨酰谷氨酰胺雙肽強(qiáng)化早期腸內(nèi)營養(yǎng)治療的臨床研究
- 血必凈注射液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社區(qū)獲得性肺炎的臨床觀察
- 孟魯司特聯(lián)合布地奈德治療支氣管哮喘患兒的臨床觀察
- 美羅培南聯(lián)合萬古霉素鞘內(nèi)注射治療開顱術(shù)后顱內(nèi)感染的臨床觀察
- 康復(fù)新液聯(lián)合重組人表皮生長因子外用溶液治療維生素B12缺乏型萎縮性舌炎的臨床觀察
- 替吉奧聯(lián)合三維適形放射治療中晚期食管癌的臨床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