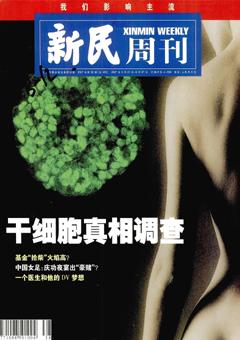金獅獎的題外話
汪 偉

只花了三年時間,李安就加入了兩屆金獅獎得主俱樂部?這是電影節(jié)主席?白胡子的中國通馬克·穆勒個人的勝利,也很可以使關心華語電影的人開懷?
李安仍然用慣有的低調,和一點冷幽默,來詮釋自己的成功?如此迅速的走紅,的確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低調和幽默證明,李安沒有被走紅沖昏了頭腦?不知道為什么,他讓我想起了金獅獎的另外兩位得主,張藝謀和賈樟柯?
對很少幾位中國導演來說,歐洲電影節(jié)越來越像糟糠之妻?從參賽者到大獎得主到評委,一圈下來,當年相看兩不厭,到如今知根知底,偶爾還要拌拌嘴,花了十幾年的磨合工夫?盡管一日夫妻百日恩,盡管老歐洲仍然風韻猶存,但激情漸漸逝去,卻是不爭的事實?她屬于往事,屬于遺跡,屬于馬克·穆勒的白胡子,屬于遙遠的1980年代;他卻還在展望未來?中年危機中特有的貌合神離開始顯露出來?這時候,奧斯卡以一場激情戲登場,挑逗有方,散發(fā)出新歡特有的氣味?正是這種氣味讓開始顯露出疲態(tài)的中國第五代神往并且興奮?張藝謀?陳凱歌,甚至馮小剛,都鼓足余勇,在向奧斯卡進發(fā)?
誰在意威尼斯連續(xù)三年把大獎頒給華語電影?答案是至少賈樟柯在意?2006年的金獅獎是他的電影生涯的轉折點?日光底下無新事?柏林?戛納同樣也是張藝謀的里程碑?歐洲電影節(jié)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們共同的成年禮?不同的,賈樟柯正享受著激情四射的蜜月,而張藝謀勉力維持一段平淡無奇的婚姻?
只看到威尼斯的風光,很容易使人變得虛妄;而一味盯著奧斯卡的失意,會讓人養(yǎng)成一顆善妒的心?最后,歐洲電影節(jié)和奧斯卡的沖突不可避免地發(fā)生在了中國?2006年,賈樟柯和張偉平因為《三峽好人》和《黃金甲》的檔期分配大吵了一架,這一架把他們的虛妄和嫉妒都吵出來了?
中年人的嫉妒是一味毒藥,加上脾氣霸道,這毒藥的藥力就來得更猛,張偉平給人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很糟糕?但很少有人覺察到,其實虛妄一樣是有害的?《三峽好人》在中國市場上遭遇的不公平被電影在威尼斯的成功夸大了?在那之后,賈樟柯談到中國電影的時候,口氣就變成了救世主式的?這是一個為自己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的救世主?激烈地批評權力與商業(yè)可恥的結盟時,賈樟柯絲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想到他那些功成名就的同行花費了無數金錢去追求奧斯卡,他卻誠實地表現著中國的生活,這驕傲并不能說是沒來由;但讓人迷惑的是,是這份驕傲使賈樟柯獲得了金獅獎?還是金獅獎讓賈樟柯變得過于膨脹?
賈樟柯和張藝謀現今已經很不相同?他們的電影仍然是在中國拍攝的?但在外人看來,他們拍攝的似乎是兩個中國?不同之處是如此醒目,加上媒體樂于看到他們互相掐架,他們的相似已經被遺忘了?
他們都有一部或者更多被禁止在國內上映的電影?這些被禁止的電影都和歐洲電影節(jié)有著種種關聯(lián)?但從《英雄》上映開始,幾乎沒有人提起張藝謀還拍過一部叫作《活著》的電影;而《世界》上映之后,賈樟柯此前8年拍攝的4部從未在中國公映的電影,也漸漸退出了議論?遺忘帶來的損失比想象的還要大?目下爭吵的話題,終歸不過是一些浮沫,真正堅硬的電影內核是什么?喧嘩淹沒了什么可貴的創(chuàng)作思想?
我想說,忘了歐洲吧,忘了奧斯卡吧,可是不要忘了被禁止的電影?但現實中遺忘的方向卻與此相反?我很難弄明白,歐洲電影節(jié)和奧斯卡是人性中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還是人生中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如果是后者的話,人生豈非是一場悲劇?
真沒有更好一點的選擇嗎?在這個時候,我才認識到,李安是另一種可能;不是因為他橫跨歐美的成功,而是他仍然保持著自嘲的勇氣和幽默感?迄今為止,他還沒有說過什么為國出征或者代言時代之類的鬼話,只是親手剪輯了內地版的《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