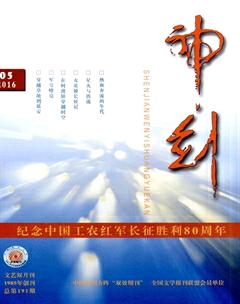穿越草地到延安
凌仕江
草地對于當(dāng)過兵的我來講
只是一個遙遠的地名
可每當(dāng)它出現(xiàn)在詩人筆端
或者歌者音符里
我都能聞到它燃燒的
嗤鼻的滾燙的體溫和余香
甚至還有血的味道
那是谷娃子帶傷的血
是戰(zhàn)友們一路流淌的血
遺憾的是我無力幫你包扎傷口
可你忍著疼痛的傷不僅替戰(zhàn)友包扎傷口
也用敵人的身體填補草地傷口
在千遍萬遍讀不完的長征詩卷里
陽光與雪水遏止不了血的沉痛漫延
月光追過的風(fēng)
每一縷都縫補著草地到延安的距離
那是一個戰(zhàn)士從故鄉(xiāng)到戰(zhàn)場的距離
站著睡覺的馬匹一眨眼
看見篝火中趕路者閉上的眼睛
驚天動地的嘶鳴如山河破碎
你咬破嘴唇不哭 你
每掩埋一位離鄉(xiāng)者的尸骨
像是習(xí)慣了帶著故鄉(xiāng)上路
那充滿荊棘的征程每一步都心如刀割
從此草地成了我駐足凝望的地方
干枯得近乎熱烈的草兒
好比一個孤兒蠟黃的面孔
一粒從故鄉(xiāng)出發(fā)的谷子
穿著自己用布條與草繩打的草鞋
穿越塵埃穿越風(fēng)雪
穿越死亡
長征再長沒有你的腳長你三過草地
踩過一個又一個沒有星光的長夜
終于在陜北的窯洞里生根發(fā)芽揚花結(jié)穗
一粒谷子的夢想多么鋒芒
可在你的人生履歷表上只有戰(zhàn)士和班長
與你同期入伍的戰(zhàn)友早已是團長旅長
可職務(wù)高低從未影響一個戰(zhàn)士的渴望
你渴望成為一發(fā)勇猛的子彈
是子彈就會在黑暗中锃亮
是子彈就該去前方
是子彈就要射向敵人的胸膛
來自五湖四海的戰(zhàn)士們都這么想
換作我也會這么想
幸好班務(wù)會上有人修理了你的思想
前線殺敵與后方警衛(wèi)都是保衛(wèi)延安
從此棗園有了兩個辨識度清晰的聲音
一個是來自湖南湘潭的湘音
一個是來自四川儀隴的川腔
在許多人的經(jīng)驗里
只要看見你的身影
總能見到毛主席
所有的形影不離就像星星與月亮的距離
一輛華僑贈送的汽車
一個在里一個在外
日曬也好雨淋也罷風(fēng)風(fēng)塵塵
在你心里保衛(wèi)好毛主席與保衛(wèi)延安一樣重要
多年以后
我一次次走過你穿越的草地
說著與你同樣的鄉(xiāng)音
而你卻早已生活在別處
如果我的詩歌能夠抵達你的延安
何必奢求那么多遠方
在湘音浸漬的土壤里
你讀書識字學(xué)文化
在北風(fēng)蕭蕭的寒夜里
你把孤獨當(dāng)作了一枚烈火燃燒的炭
除了站崗送信劈柴開荒種地收莊稼
你還幫那些頭裹白毛巾的鄉(xiāng)親擔(dān)當(dāng)困難
你用忠誠詮釋著一粒谷子與一枚炭的內(nèi)涵
就像我此刻用冥想詮釋你在一張紙上的分量
喜鵲在棗樹的枯枝上
吻到了第一縷綠色的喜訊
延安的冬天太冷可你從不怕冷
你脫下衣服為毛主席陷入泥潭的車解圍
你讓主席讀懂了戰(zhàn)士的真誠與奉獻
這也成為你
由通信班長到一名警衛(wèi)的重要轉(zhuǎn)折
你的心里不僅裝著主席的安危
還有炊事班啞巴腳趾縫上腫脹的傷口
那位從長征途中一路跟隨紅軍的啞巴
也是你用方言溫暖出門在外的牽掛
你用老家的草本為啞巴療傷
啞巴每次去找你遇到主席就要握手
啞巴用大拇指對主席不停表達
主席懂了啞巴的意思哈哈笑了
后來 誰都不可以阻止啞巴與主席握手
雖然那不是誰都能幸運地握手
可那注定是星星與太陽的約會
那是兩個世界的深情相擁
是無聲勝有聲的光陰溫柔
谷娃子 我的兄長
我多想去延安見你一面
如果不在窯洞前孤獨地站崗
你在戰(zhàn)場上早已是一名指揮千軍萬馬的猛將
照樣可以當(dāng)連長營長團長甚至旅長
可你靜靜地承擔(dān)了普通與平凡
我從草地來到你的故鄉(xiāng)
那些披著谷雨的秧苗很蓬勃
而我在人群中卻一直沉默
你朝北的窗是否長滿了燦燦的星斗
你存放心中的那一枚紅五星帽徽
能否借我擋一擋風(fēng)吹的塵埃與人生的霧霾
我知道那是你一路珍藏的信仰
可它真的也是我最需要的營養(yǎng)
是滿世界都需要的營養(yǎng)
責(zé)任編輯/蘭寧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