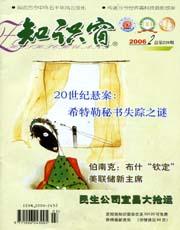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軍用高速公路
梅旭東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許多偉大的軍事工程都出現(xiàn)在秦始皇時代?在建筑史上留下彪炳千秋的阿房宮?驪山陵?萬里長城已經為世人所知,但通行全國的馳道和遠達塞外的直道知道的人卻不多?隨著對秦直道遺址的勘查和研究,秦直道開始從塵封的歷史煙云深處脫穎而出?有專家說,秦直道規(guī)模宏偉浩大,其歷史意義并不亞于萬里長城?
歷史迷霧中的偉大工程
秦直道由秦都咸陽附近的云陽(今陜西淳化縣北)北行,至子午嶺上,循主脈往北,一直到達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西)的陰山腳下?全長“千八百里”,大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700公里,路面平均寬度大約30米?由于道路大體南北相直,故稱“直道”?
直道所過之處,地勢險惡?人跡至今罕至?幾十萬筑路民夫劈山填谷,就是越過海拔1800米的子午嶺也不回避?道路的修筑用黃土夯筑,夯得非常結實,以致直道上樹木至今也無法成活,路面上只生長一些生命力頑強的野草?在某些地段,汽車仍然可以行駛,2000多年后,凄凄黃草下時隱時現(xiàn)的古道,依然讓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關于秦直道的記載,最早見于《史記》?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里說:“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在《蒙恬列傳》中則說:“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此外,就很難找出關于秦直道的記載?
秦始皇不惜國力用了兩年的時間修筑這條工程浩大的直道又是為了什么?或許,只有追隨秦始皇那支無敵軍隊的足跡,才能找到答案?
追溯遙遠的戰(zhàn)爭足跡
眾所周知,秦統(tǒng)一六國之后,先是南方土著叛亂,秦始皇歷時四年,傾國力于一役,終于在公元前215年平定南方,帝國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南海之邊?接下來匈奴人又成為秦軍最后一個對手了?北方草原上這個游牧民族對中原一直是個巨大的威脅,當秦軍在南方奮戰(zhàn)的時候,匈奴人越過了陰山腳下的黃河,直接威脅秦帝國的都城咸陽?
大將軍蒙恬揮師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決匈奴問題?但是,30萬強悍的秦軍并沒有立即與匈奴騎兵決戰(zhàn),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長城邊上?
秦軍和匈奴人周旋了幾百年,蒙恬家族幾代人都是秦國的戰(zhàn)將,他非常了解匈奴作戰(zhàn)的特點?匈奴是游牧部落,是游擊戰(zhàn)高手,他們居無定所,往來如風?如果秦軍倉促出擊,匈奴騎兵會避開鋒芒,繞到別處大肆搶掠,甚至兇猛攻擊秦軍的后方?而秦軍勞師遠征,尋求決戰(zhàn)而不得,曠日持久將無法忍受?幾經斟酌,蒙恬選擇了長城戰(zhàn)略?
所謂長城戰(zhàn)略,就是通過修補改造過去的長城,并在長城沿線修建數(shù)個由堅固城墻圍起的小城,作為戍邊軍民的居所,把它建成戰(zhàn)斗支撐點,使長城成為一個攻防兼顧的作戰(zhàn)體系?在反擊匈奴的戰(zhàn)爭中,長城戰(zhàn)略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優(yōu)越性,蒙恬大軍以不變應萬變,在北方草原上對敵堅持持久作戰(zhàn),匈奴的侵犯行徑得到了有效遏制?隨著戰(zhàn)線的拉長,作戰(zhàn)的曠日持久,后勤補給問題日益凸現(xiàn)出來,秦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供應這支北方軍隊的糧草主要來自山東半島?從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線距離1000多公里,運糧的隊伍要兩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過黃河?史書上記載:從出發(fā)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糧食才能剩下一石供應軍隊?為了向前線輸送糧草,成千上萬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處的匈奴人并沒有消失,他們隨時可能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戰(zhàn)爭,后勤運輸?shù)钠D難,是秦始皇未曾料想到的?作為帝國的決策者,他必須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秦直道,秦始皇的解決方案
通過這條直道,蒙恬軍團的戰(zhàn)略物資從帝國的都城咸陽開始,沿途綿延向北,源源不斷地運達秦九原城?當年的九原是帝國北疆的軍事重鎮(zhèn)?軍需物資從這里再分發(fā)到帝國北部守衛(wèi)長城與匈奴作戰(zhàn)的將士手中?專家估計:北部邊疆一旦有事,騎兵部隊通過秦直道三天三夜就可以從咸陽趕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內就能夠基本完成從軍隊調動到后勤供應等一系列的準備工作?700多公里長的直道,為秦帝國迅速投放部隊?及時輸送糧草,最終戰(zhàn)勝匈奴提供了根本保障?直道,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軍用高速公路?
2000多年前,只有秦人才有能力修造這樣的軍事工程?秦人建立了那個時代世界上最發(fā)達的物流通道?這些四通八達的道路為南征北戰(zhàn)的秦軍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據(jù)考古專家測定,秦直道上至少有80座郡城?直道和古棧道通連,相鄰二棧道之間,常有若干小道相通,直道有不同的出口,從而形成縱橫交錯的網狀結構?這充分展現(xiàn)出當時網絡系統(tǒng)及物流思想的光輝?
面對這條2000多年前的軍用高速公路,我們不禁感嘆扎根于神州沃土的“物流實踐”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