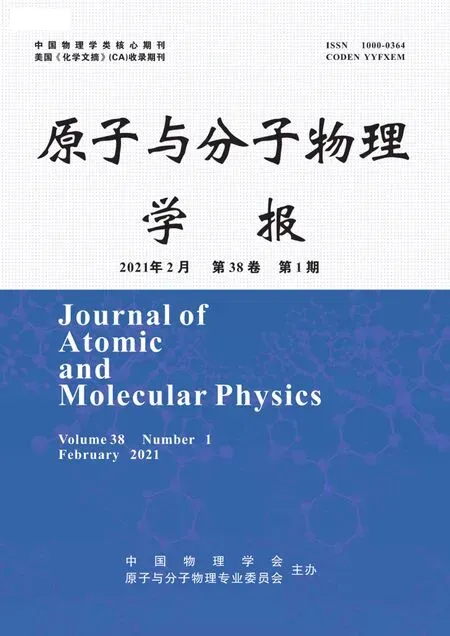Mo摻雜4H-SiC的磁性和光學(xué)性能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2021-03-29 07:29:26郭瑞賢,蘇晉陽,劉淑平
原子與分子物理學(xué)報(bào) 2021年1期
關(guān)鍵詞: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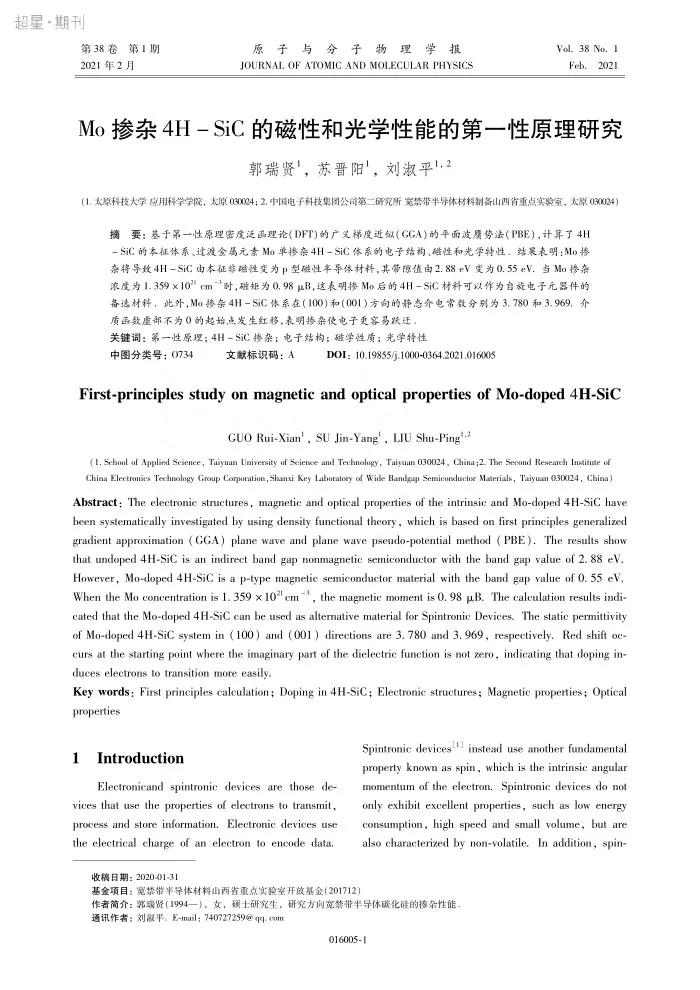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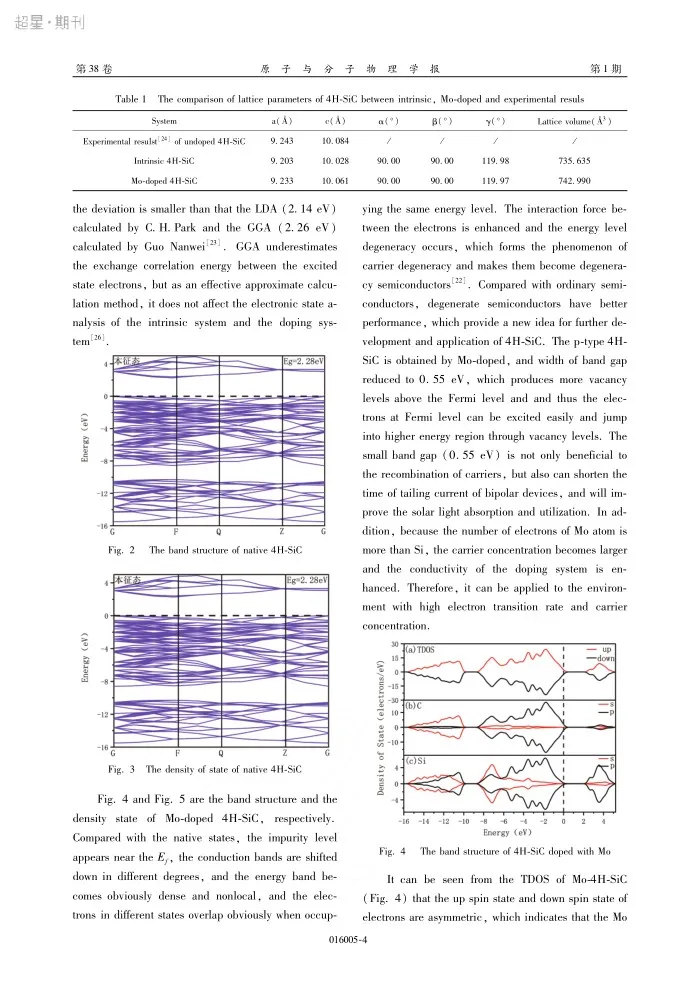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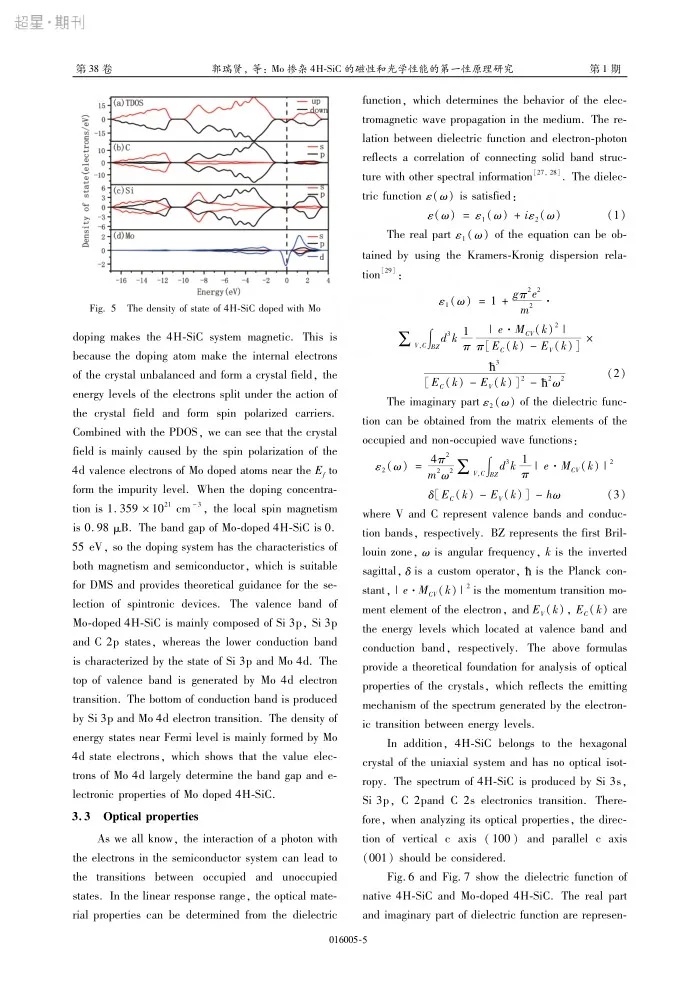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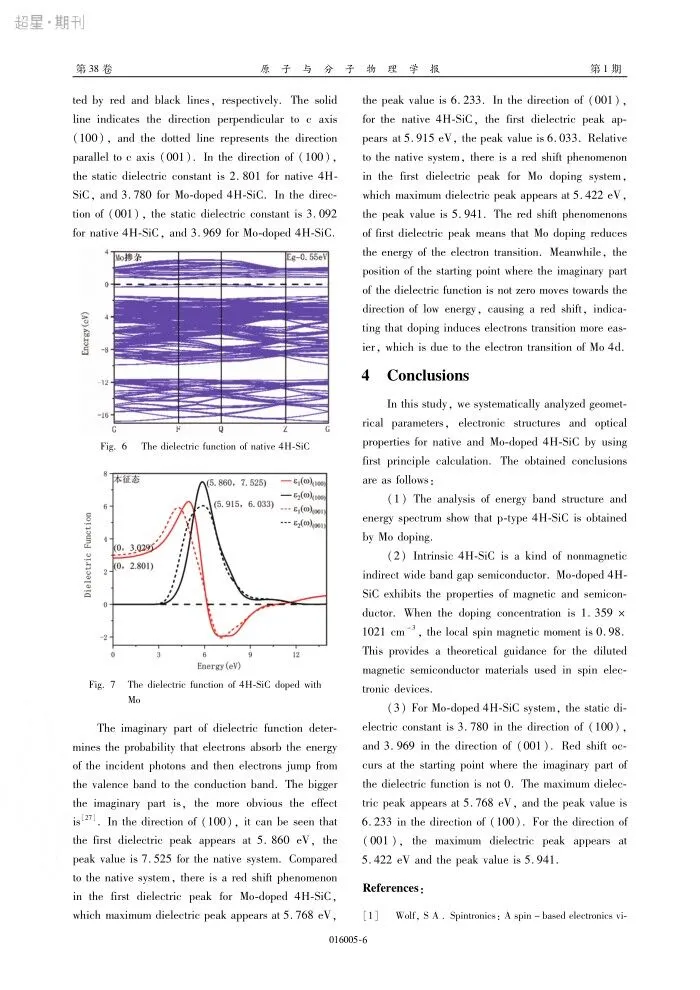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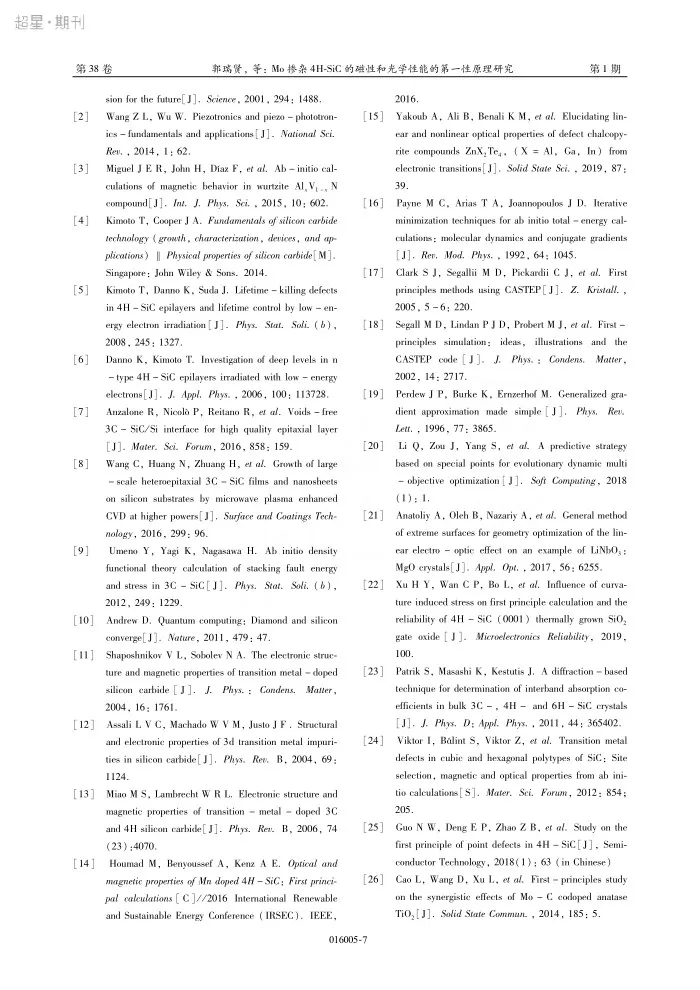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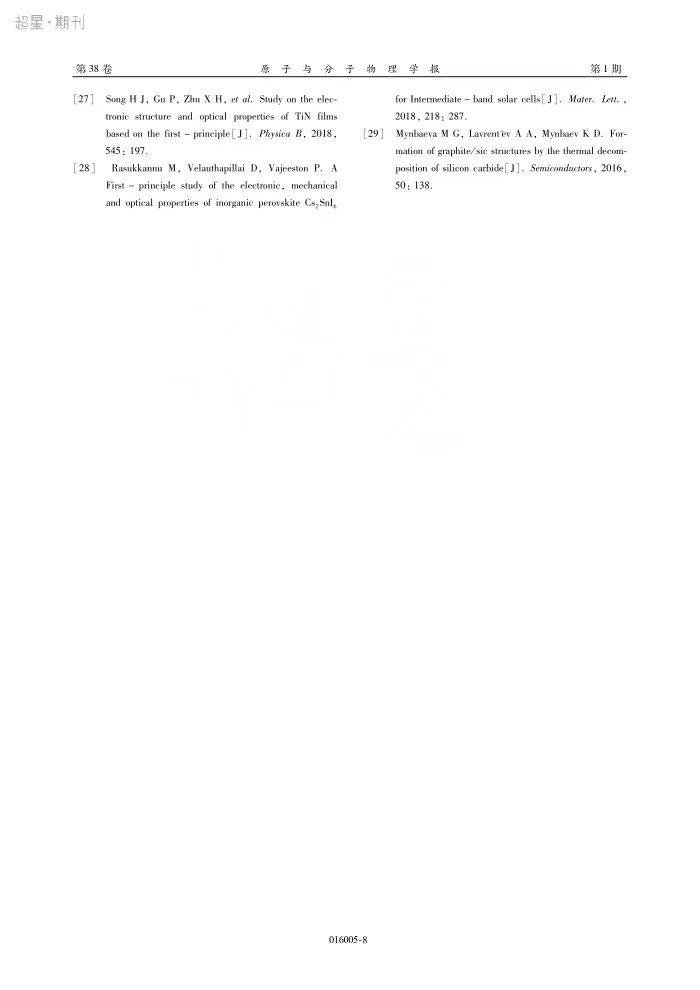
猜你喜歡
體育科技文獻(xiàn)通報(bào)(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5:20
民用飛機(jī)設(shè)計(jì)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電子制作(2018年11期)2018-08-04 03:26:04
汽車工程學(xué)報(bào)(2017年2期)2017-07-05 08:13:02
國際商務(wù)財(cái)會(2017年8期)2017-06-21 06:14:14
電子制作(2017年23期)2017-02-02 07:17:19